今天
光明日报《文化周末》栏目刊发了
题为《橙满园》的文章
通过散文的形式
讲述了七星关区清水铺镇
橙满园的“前世今生”

全文如下↓↓↓
一
秦朝的时候,这里虽辟出一条五尺道,但漫山是萋萋荒草。千里奔涌的鳛水,沿着山脚咆哮而去。常常有兵马顺着五尺道赶到岸边,然后利用吊桥,渡过惊涛雷吼的鳛水,由黔中郡涌入对岸的蜀国。修建吊桥需要砍伐竹竿或者树木,捆绑后搭在绳索上,甚至还会用铠甲充当桥面。附近的几户百姓听到动静,早已仓皇逃遁。
见秦国军队远去,隐身于山林的百姓,才敢壮着胆钻出来,继续坐在河滩上,修补破旧的渔网,或栽种葵菜和藿菜。太阳西沉,忙碌的百姓陆续返回自己的茅草房。这家的妇人用藿煮汤,以菽制豆饭,勉强填饱男人的饥肠;那家的妇人用陶簋端上的食物,却是以麻的籽实所制成,男人食之,“蜇于口,惨于腹”。
这条河,因“流卷泥沙,每遭雨涨,水色浑赤”,得名赤水河。明洪武十五年(1382年),在河岸置赤水卫。相比秦朝,这条河并不像千百年前那样来势凶猛,非要开山劈石。它在光阴里消瘦,也变得更加温顺了。
彼时,路上已经出现马帮,驮着茶盐往返不绝。马掌撞击石头的声音,响彻四野。
河两岸人烟稠密,附近百姓对马帮也习以为常,他们老是端着酸菜包谷饭,站在自家的场坝远远近近地张望。路途迢遥,马帮常在村庄落脚,多种文化也在此交汇,新老文阁、赵家祠堂和江西会馆、观音寺、寿福寺等建筑陆续建成。
这里热闹非凡,但真正的转机,却发生在清代末年。
据传说,那是一个凉爽的季节。运盐回来的马帮在驿站休整过后,准备往贵州毕节进发。几名赶马人走出石板街,顺着千年古道往上爬。行至山腰,他们取出几个从四川带来的皱皮柑,剥掉皮后就往嘴里塞。他们把剩余的籽顺势吐在路边,奔涌的河风卷来尘土,盖住了那些遗留的种子。
半个多月后,从土里拱出了嫩芽。随着气候变暖,嫩芽舒展叶片,呈现出蓬勃生机。大家并没有留意那株幼苗,一些路过的孩童,甚至还往上面撒尿。果树苗茁壮成长,绿油油地站在古驿道的边上,但因挂果缓慢,仍未取得关注。曾有村民的锄把坏了,打算用它重做一根,但折断枝条,却发现材质不够坚硬,只能放弃。
粗粝的风呼啸不止,它从山前奔来,再往山后奔去。卷起的尘土落在叶片上,根本没有谁料到,这棵灰头土脸的树,将带来一场巨变。在挂果之前,它都注定默默无闻。倘若它生长在地里,即便再无用处,也要被连根刨起,腾出位置栽种粮食。幸运的是,它长在地埂上,既未抢占庄稼的养分,也没阻挡马帮的去路,因此能够顺利存活。
在光照强烈的时节,土地的主人需要找地方乘凉。只有在这种时候,他才会想起这里还有一棵陌生的树。马帮经过驿道,虽然知道这是一棵皱皮柑树,但因没有果实,也并不在乎它的死活。赶马人想歇脚,随手就往上面拴骡马,将树皮磨破了。伤疤还没痊愈,接着又被磨破,只因它是一棵“无用”的树,必须忍受这份疼痛。如此反复,裂开的树皮让它营养不良,叶片几度枯萎发黄,甚至因丧失水分,而差点断送生命。庆幸的是,尽管这棵果树饱受磨难,最终还是坚韧地活下来了。
大约八九个年头之后,这棵顽强的皱皮柑树终于挂果了。果实由青变黄,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有人剥开它丑陋的外壳,内容饱满。放进嘴里品尝,竟酸甜可口,汁水充盈。
这块土地的主人当即出来认领,声称这是自己栽种的东西。尽管主人严防死守,但邻居经常在夜色的掩护下,成功偷走树上的柑子。土地的主人急得破口大骂,却无计可施。次年的中元节,主人终于想到一个办法。他多次在深夜偷偷来到树下,制造出各种诡异的响声。没过多久,村里就传开了,大家都说那棵树“成精了”。
唬住盗贼,土地的主人起先还感到高兴,后来却连他自己也不敢再摘上面的果实。因为,他发现那棵树上竟慢慢挂起了醒目的红布,树下还有香纸的灰烬。在深山里面,历来有祭拜神树的风俗。大家认为万物有灵,凡是供奉过香火的树,都不能再随意触碰。望着挂得越来越多的红布,土地的主人也跟着害怕起来。他渐渐相信,这棵树的身上已有灵性。
二
1963年,有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孤身走在驿道上。当时,这条驿道盘踞的地方还叫毕节县,直到多年后才改名七星关。那个年轻人被分配到毕节县农业局工作,却因县城已无岗位,只能下到乌蒙深山。
年轻人需要通过这条古驿道,前往那个隐藏在河谷地带的村庄。由于来自温暖的东海之滨,他有些难以忍受云贵高原的寒冷。路上的荆棘不断划破年轻人的脚板,让他受尽折磨。他费尽力气,翻过无数荒凉的山头,却迟迟不能看到目的地。他沮丧地坐在驿道上,怀疑自己根本无法走完这段旅途。
路面的石块在岁月里失去棱角,马掌磨出的印迹清晰可见。杂草顺着缝隙钻出来,让这条千年驿道尽显沧桑。年轻人几次想转身返回,但来路和前程,同样遥不可及。他鼓足勇气,顺着驿道继续往前。当他踩着夜色走进村庄,刚把皮囊拖到床上,就迅速滑进睡眠。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,年轻人终于恢复精神,只是他还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在随后的半个月里,年轻人每天清早起来,弯着腰在驿道上寻找,直到暮色四合,才失魂落魄地回到屋里。
年轻人的异常举动,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他们以为年轻人丢了钱财或者钥匙,于是热情地跑来帮忙。他们跟在年轻人的身后,用木棍挑开草丛,沿着道路仔细搜索,但连续几天一无所获。
最后,他们围在年轻人的身边,问他到底找啥?年轻人满脸茫然,说自己也不晓得找啥。村里人感到被捉弄,顿时散掉了。蜿蜒的古驿道上,仅剩年轻人孤零零一个。他并没有因为队伍的散去而放弃,仍在那里固执地寻觅。那天晌午,两个老者坐在观音寺旧址晒太阳,他们看着远处的年轻人议论。其中一个老者说,他肯定是“魂掉了”,所以在寻找自己的魂魄;另一个则很有把握地回答,他在“捡”自己的足迹……
年轻人仍旧早出晚归,不断寻找。村民都在怀疑,他的脑壳出问题了。
有一天,年轻人抬起头,看到山上红布飘展。他顺着驿道往上走,来到那棵赶马人吐籽而生的皱皮柑下,终于停住了脚步。他围着皱皮柑树连转两圈,然后靠着树身疲惫地坐了下去。落日映射在身上,让他身上仿佛也挂满红布。
当太阳坠落后,悄无声息的黑暗,慢慢将他封存起来。山里的夜色,比任何地方都要浓郁。周围除了晚风吹拂,再也不见别的东西。年轻人听到自己的呼吸,感到世上只剩自己孤零零一个。恍惚之中,他甚至觉得身体也在融化和消失。第二天清晨,东升的太阳把年轻人拯救出来,重新归还于世界。
年轻人挣扎着站起来,他没再寻找别的东西,而是跑回屋里。村民都以为年轻人会睡上一觉,没想到他却拿着一把刀,沿着古驿道,重新奔向那棵皱皮柑树。他准备截取枝条,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知识嫁接果树。
村民们慌忙拦住他,说这是一棵有灵性的神树,千万不能动。年轻人说,如果招来灾祸,我独自承担。村民说,你能够承担倒好,就怕牵连大家。
年轻人打算采果育苗,仍然遭到阻止。村民警告说,村里有个娃儿,偷摘柑子来吃,第三天就被赤水河卷走了。
年轻人没再争论,而是终日守着那棵“神树”。村民困惑地问,你在搞啥名堂?
年轻人说,我等柑子自己掉下来。皱皮柑树挂果时间长,年轻人很多天才能捡到一个柑子。每次他都像捡到金元宝似的,捧着往回跑。
他从树林寻来肥沃的黑土,掺上秸秆和牲口粪便,均匀地撒在挑好的土地上,再将抠出来的种子放在清水里漂洗,并进行浸种催芽。嫩芽冒出来后,栽进用食指按出的坑洞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,秧苗终于破土而出。在此后的岁月里,那棵神树的“后裔”陆续被移种到田边地角。短短几年,就占据整个村庄。
村民用破旧的背箩,将新鲜的水果背到街上出售。其他村的人围过来问,这是啥东西?村民回答,这是我们那里的“神果”。
于是,方圆几十里都知道,那个村庄有一种甜得要命的“神果”。县里的领导听到消息,让村里摘几个送去。村里派一个壮实的汉子,扛着几十斤果实进城。县领导打开麻袋一看,当即阴沉着脸,让壮汉捎话回来,说不要搞封建迷信,这是皱皮柑。
村里干部得到指示,马上放出话来:谁再说这东西是神果,就罚他开垦荒地!
大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处罚而屈服,他们每天扛着锄头,上山挖石头。他们一边将坡上的石头刨出来,砸碎后堆砌地埂,一边嬉笑打闹。村干部改变策略,声称谁再胡说八道,就把他家地边的果树砍掉。这招果然奏效。当其他村的人再来采购水果时,这里的村民总是告诉他们:这不是神果,而是皱皮柑!
三
村庄不仅有皱皮柑树,还陆续出现其他的柑橘树和橙树,甚至因为柑橙繁茂,这里改名叫橙满园。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,像是突然出现的灵魂,将它和其余的村庄区别开来。即便藏身乌蒙腹地,方圆百里也都知道它的存在。绵延起伏的乌蒙山上,草木在时间里枯死,也在时间里诞生。它们看似亘古不变,实则瞬息万变。
那个年轻人就像所有的过客一样,并没有在驿道上留下明显的痕迹。但古驿道上那些坚硬的石板,却被这些后来者的脚步磨得更加锃亮。所有的道路,都因为前行者和未来人而改变。每一个经过的人,都在删改世界的细节。橙满园的景象,也悄无声息地变化。年轻人通过赤水河上的铁桥,从遥远的地方引进新品种,并经过多次培育和嫁接,让它们呈现出全新的面貌。
年轻人栽培果树的时候,自己同样变成了一棵树。16年的光阴,让他在橙满园根深蒂固。
当他接到调离通知,竟满脸茫然。半晌过后,他才想起自己只是一个游子。既然是游子,就注定要回到故乡。
那个不再年轻的游子,踩着古人的足迹离开了,但果树已经占领了村里的每一块土地。那些树举着红澄澄的果实,像举着灯笼送他远行。(作者:曹 永,系中国作协会员,现居贵州毕节)

插图:郭红松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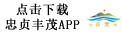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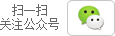


 公安机关备案号:
公安机关备案号:




